最好的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pf/a_7534559.html
编者按
年第4期,本刊曾选登了数篇选自第六期“中国近代史论坛”的稿件,其中,探讨新式“器物”和“技术”如何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制度变革、文化生产、知识传播等进程的论文给人以深刻印象。这组论文向我们展示,在晚清以降人们所感受的巨大“世变”中,传播媒介方面的技术进步与广泛应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是进一步探讨“器物”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深层联系的一个尝试。第八期“中国近代史论坛”正是沿袭了这一脉络,集中探讨快速演变的物质文化形态如何在迅速改变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对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形成强大冲击。本次论坛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讨论。第一,近代物质文化演变本身。诸凡生产领域、流通领域、消费领域、传播领域、艺术领域,诸凡设计、技术、流程、工艺,诸凡传承、引进、融合、创新,诸凡实用功能、文化意义、审美情趣、匠心匠意,等等,均在与会者视野之内,既有一器、一技、一艺的细绎,也有贯通纵横的论述。第二,物质文化对生产方式、管理模式、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生活形态、大众心理、时空观念等方面的影响。第三,近代道器关系宏观省思。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基本出自本次论坛。
作者赵婧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年第5期,注释从略
柳叶刀尖——西医手术技艺和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
赵婧
内容提要
19世纪中叶,西方基督教医学传教士用柳叶刀所象征的手术技艺打开了西医进入中国的大门,展示了以外科方式治愈某些身体病痛的新途径。麻醉术、无菌术等与外科密切相关的知识和技艺传入中国并不断更新,更奠定了西医以外科见长的医学论述基调。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西医论争中,西医手术成为判定中西医优劣、内外科强弱的焦点之一。西医外科超越器物层面,兼容医学各科之发展,其学科界定直指中国传统医学的“落后”医理。中医在反击西医外科优越论的同时,也经历了自我重构的过程。从采生折割的恐怖想象,到西医手术的逐渐采纳,医院为代表的新式治疗场域内,恐慌与疼痛的体验并存,充满着医患之间的复杂博弈。西医手术既以刀割技艺疗治国人身体,也逐步形塑了新的医疗理念与身体观念。
关键词
西医手术;外科史;手术技艺;身体观;医疗行为
绪论:重返手术现场
就西方医学史而言,19世纪无疑是外科革命的世纪。现代外科学及其技艺的长足发展,与现代解剖学、麻醉学和无菌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维萨里(AndreasVesalius)于年出版的《人体的构造》(DeHumaniCorporisFabrica)一书奠定了现代解剖学的基础。18世纪以后,外科医生承袭了维萨里的学说,认为可以凭借这种精准、细微的解剖观察,打造属于外科学的独立知识体系,解剖学成为外科医生迫切需要的“有用知识”。一千多年来用全身体液不平衡来解释疾病发生的理论,开始受到质疑。至19世纪早期,解剖学视野下的局部身体病灶,被认为非常适合以外科的方式来处理。
在细菌学和消毒技术主导医学的时代到来之前,体液学和整体医疗的思路是西医理论的主流。就体表创伤而言,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化脓有益”,或曰“可称道的脓”。根据古罗马著名医学家盖伦(ClaudiusGalenus)的论述,血液意即营养体液,在愈合过程中会蓄积在伤口内,变成脓液,因此某些化脓现象可视为伤口情况好转的指标。对此存疑的英国近代外科学家李斯特(JosephLister)受巴斯德(LouisPasteur)细菌学说的启发,通过试用各种消毒液,试图在手术部位和手术室范围内全部灭菌,以对抗伤口感染与化脓。年,他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Lancet)上发表此论见,由此开启无菌外科时代。
李斯特在无菌手术发展历史上的贡献使得英国外科大放异彩,而麻醉应用于外科手术则是美国对医学的贡献。19世纪中叶,乙醚、一氧化二氮(笑气)、三氯甲烷(氯仿或哥罗芳)等麻醉剂在美国被数名外科医生先后使用,很快即传遍整个欧洲。年10月,莫顿(WilliamMorton)在医院进行乙醚麻醉术的公开演示,被视为现代麻醉学诞生的标志。美国医生常用乙醚做全身麻醉,而英国医生则偏爱氯仿。而在此之前,大型侵入性外科手术现场通常是充满叫喊、异响与血腥的恐怖场景,外科医生对始终清醒的患者大动干戈,为了减少疼痛、休克与失血量,手术飞快进行,但死亡率仍居高不下。
若干世纪以来,以内科为主导的医学界始终对外科持鄙夷态度。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誓言曾提到,医生应该避免外科而让其他人去实施手术。从西方医学之父开始,外科明显地被视为较为另类的行当,因为它是手的工作,而不是脑的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科始终被称为“理发匠的技艺”,被从正统医学中剔除。相对于承袭了悠长博学传统的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地位很低,被讽刺为屠夫或虐待狂,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与淋漓鲜血为伴,使用的外科器械也是令人恐怖的,如刀、烙铁、锯子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外科的近代史即是摆脱上述污名、建构自身正当性与科学性的历史。启蒙运动强调实践而非书本学习,促生了将外科视为科学的观点,这大大推动了外科的进步,提高了其在医学专科中的地位。外科医生将“操作技术”定为专业核心,并声称自己所从事的是“科学外科”,这符合启蒙时代士绅阶级追求的目标。随着19世纪下半叶外科革命的推进,外科从技艺上升为科学实践,与此相应,外科从业者从因经验习得技术的熟练匠人,演变为经过严格的解剖学和病理学训练的专业人员,地位迅速提升,在治疗过程中也变得越来越主动。
至20世纪上半叶,西医外科临床实践发生巨变。外科日益细分化、专业化与普遍化,外科手术风险与死亡率逐渐降低,大型侵入性手术不断增多。外科医生的工作不再是若干个世纪以前那种常规、小型和相对安全的手术(如包扎伤口、拔牙、处理性病的下疳和疼痛、处理皮肤瑕疵等日常治疗),最普通的外科操作也不再是被视为外科职业象征的放血术,而是越来越普遍的阑尾、扁桃体、子宫、疝等部位的切除术。
有关西医外科学及其发展史,在20世纪中国人书写的医学史中常有论及,专书有丁福保《西洋医学史》中的《外科学史》、刘兆霖《外科史》等。两书皆详述西医外科的线性历史进程以及外科医生的伟大成就。国人编译的此类西医外科史,除了彰显西医手术“器械之精良、刀具之锐利”之外,意在刺激中国医学的觉醒与崛起。19世纪中叶西方教会医学入华之初,西医外科知识与技术乃西医区别于中医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教会医学用手术技艺打开了西医进入中国的大门,吉利克等学者有关伯驾(PeterParker)、合信(BenjaminHobson)、德贞(JohnDudgeon)等医学传教士的研究,展示了他们如何通过手术刀开辟了西医扎根中国的路径,并奠定了西医以外科见长的医学论述基调。20世纪以后,随着西医手术的逐渐普及,名人手术个案引发的中西医之争,使得西医手术的话题更大范围地闯入公众视野,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孙中山割治肝癌、梁启超“割错肾”等医疗个案。此外,相关医学器物与技术的传播(如X光机、显微镜、听诊器、注射技术等)为外科手术的诊断与治疗提供了新的知识与方法,由器物到技术再到观念,参与形塑了国人新的身体观与医疗行为。对此学界也有所





 当前时间:
当前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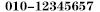 E-Mail:
E-Mail: